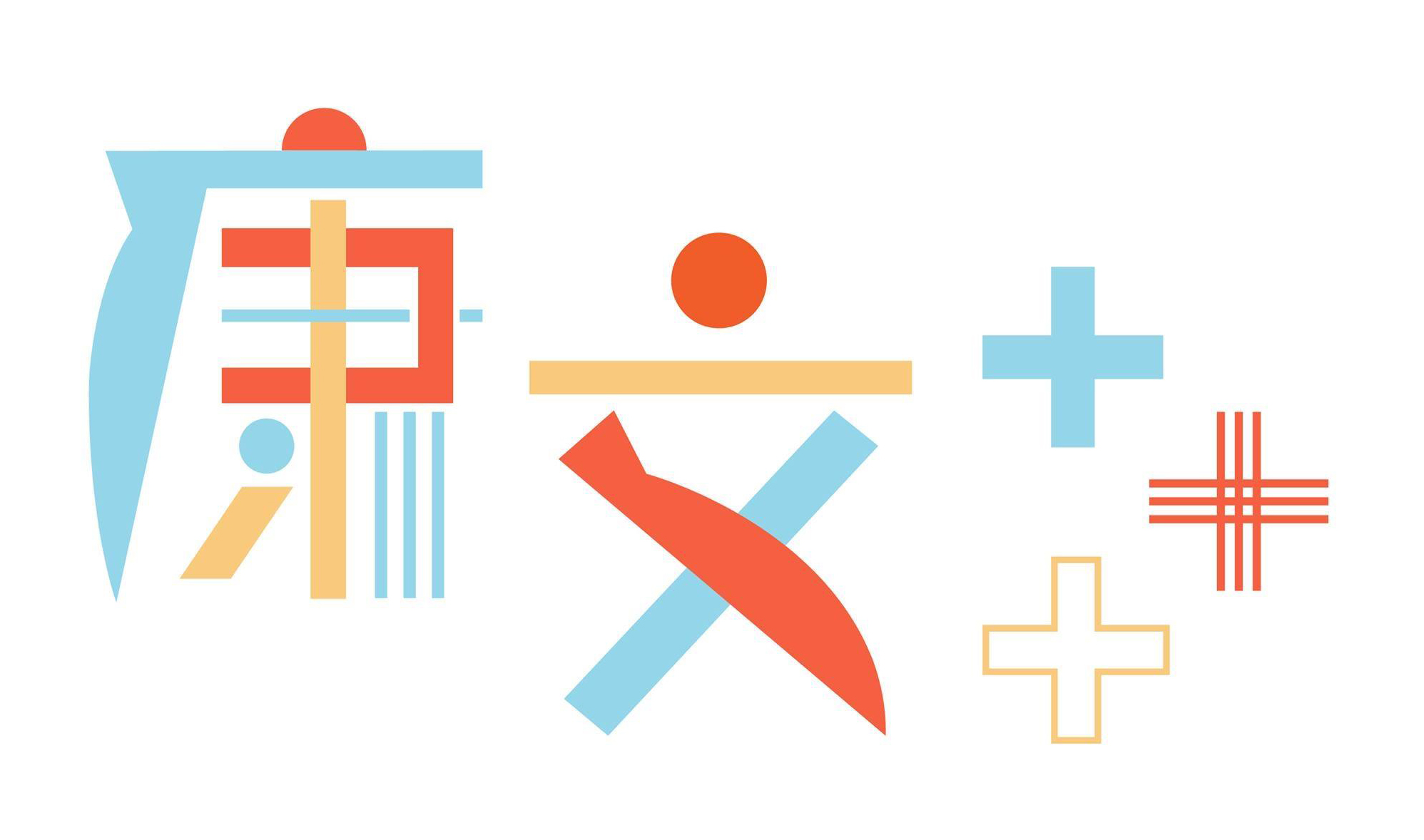专题文章
红香炉与红香炉天后庙
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
丁新豹博士
1999年
在英国人的认识中,香港就是香港岛的总称,无论文献记载,以致绘制的地图皆如是,英国人占领港岛后,香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岛的官方总称。但在此之前,在中国的官私文献中,香港指的是全岛一隅的香港村,即目下黄竹坑一带地方,文献在提到香港岛时,往往罗列出岛上村庄的名字:大潭、裙带路、赤柱、红香炉、筲箕湾、黄泥涌、薄凫林,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总称。正因如此,在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代表琦善和义律在商议割让香港时,便曾就"香港"的定义问题引发过一场争论。1
"红香炉"曾是香港岛的总称
在上述芸芸的地名中,"红香炉"曾被用作香港岛的总称。万历年间(1573-1620)郭编撰的《粤大记》所附海图,标示了港岛上七条村的名字,其中包括香港、筲箕湾、赤柱、大潭、黄泥涌等,说明了在明代,港岛上已有多条村落。编撰于清初复界后的杜臻的《闽粤巡视纪略》,记述了港岛上多条村庄受到迁界的影响,复界后已先后恢复;康熙廿七年(1688)靳文谟编的《新安县志》,提到黄泥涌及香港村,但均不见"红香炉"之名。2据知"红香炉"一名,首见于王崇熙:《新安县志》〈兵制条〉;阮元在道光二年(1822)编的《广东通志》指出:
"红香炉水汛:在本营西,水程二百九十里,下至大鹏山炮台,水程一百一十里,千总一员,外委一员,该汛兵丁拨配米粮巡洋。3
红香炉汛创设于何时,论者皆说是干嘉年间,但确切年份不详。但陈伦炯着的《海国闻见录》的沿海图中,标示出"红香炉山",按位置论,应为香港岛无疑。查陈伦炯自幼随父出征,对东南沿海形势熟悉,复擢为东南沿海副将及总兵,其《海国闻见录》,是按他搜集的沿海形势资料及海防策略集编而成,于乾隆九年(1744)刊行4,可说明"红香炉"一名,至迟于乾隆年间已出现,而且已是整个岛的总称。王崇熙的《新安县志》(1819)记录了新安县治下的村落,并无"红香炉"之名,但此书附录的海图,却把红香炉及赤柱,标示为两个岛屿。5此图似偏重于沿海海防建置,而红香炉及赤柱均为港岛上的汛站6,故图中特别标出两汛站的名字与位置。反观陈伦炯的海图有"红香炉"一名,亦可能因为要突出红香炉汛的战略地位,陈伦炯长年于军旅中生活,对海防建置格外关注,理所当然。
文献中有关"红香炉"之记载
现存海外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多幅海图,都标注出"红香炉山"或"红香炉汛"以作为香港岛之称谓,如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"《广东沿海图》,可能摹自嘉庆年间绘制的地图,"香港"二字未出现,而标上"红香炉山";现存大英图书馆的《广东沿海图》,内容和形式与上图相近,也是标上"红香炉山";而另一幅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《粤东洋面地图》,可能是以陈伦炯《海国闻见录》所附海图为蓝本,"香港"标于"红香炉"之左下方,红香炉岛上画上营汛标志。7
这种以"红香炉汛"或"红香炉山"作为香港岛总称的习惯,显然是红香炉设汛后开始的,陈伦炯的海图标出"红香炉山",其摹本或派生本便萧规曹随,依样胡芦。晚至同治三年(1864)编的《广东通志》的海图,仍以"红香炉汛"为港岛之总称8,此书成书时,上距英国割占香港已有22年,所有原来军事建置及驻兵早已撤走,但仍沿用旧称,一方面可反映出国人对绘制地图不重视,不认真,只懂抄袭模仿,不肯作实地勘测或时加修订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红香炉在地图上作为香港总称,显然与红香炉汛分不开的,清代海图,往往突出汛站所在,到后来,便索性以汛站名称作为该岛之总称。
必须指出:据中国文献记载,红香炉只是汛站,不是村庄,所以王崇熙的《新安县志》所列村庄并没有红香炉之名9,但汛站还是有驻兵的,闽浙总督颜伯焘(?-1855)在道光廿一年(1841)的奏摺中说:
"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,其岛曰红香炉,上有营汛居民,并非偏僻小岛可比。"10
又英人占领香港岛前,英军司令伯麦(Commodore J.J.GordonBremer,1786-1850)曾照会中方大鹏营协镇赖恩爵将军,促"速将该岛全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"11,可证明港岛上一直有营汛驻兵,直至英军登陆前才撤离。
据1841年5月15日《香港辕门报》(Hong Kong Gazette)所载香港岛在开埠伊始时的人口分布情况12,岛上除去已无人居住的废村,共有16条村,其中包括了"红香炉",有居民50名,是一条小村,论人口,它排在赤柱(2,000),筲箕湾(1,200)、黄泥涌(300)、香港村(200)、亚公岩(200)、石澳(150)、土地湾(60)之后,而在扫杆甫(10)、西湾(30)、石塘咀(25)之上、与群大路相同。查歌连臣上尉(Capt Collinson)于1845年绘制的香港地图,大坑一带沿着注入铜锣湾海旁的水坑(大坑即以此得名)尽是稻田13,可以想见,红香炉的人口实则上应包括了大坑住民在内。开埠前后,红香炉这个原来的汛站终于成为一条村庄了。居民有黄、张、李、朱、叶等姓,都是客家人。到1911年,大坑的人口已增至1,57414,但红香炉的名字,却渐渐湮没无闻。
"红香炉"名字之传说
红香炉一地因何得名,一个说法是:
"有一天,海面上有一个大香炉被水冲到岸也来,被当地乡民和渔民发现,便将香炉捞起。渔民和乡人,认为这香炉一定是天后娘娘送来此地的,便叫人上香奉祀,和在该处建一小庙,用这个香炉来上香,由于灵验之故,庙貌便发展起来。"15
另据铜锣湾天后庙戴姓庙祝所述,该庙乃其族人所创建,戴姓族人来自淡水的客家人,先居蒲岗。据说,其族人常渡海至港岛沿岸割草,一次于岸边发现一天后像,乃于发现地点兴筑一简陋神龛予以供奉,后来香火渐盛,庙宇乃扩建云…..。16上述当然是神话传说,但红香炉传说与红香炉一地及红香炉天后庙,显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据约翰斯顿(A.R.Johnston)的记述,开埠时,港岛上已有多间庙宇,其中规模较大的是:赤柱天后庙、香港仔的天后庙、鸭洲的洪圣庙及红香炉天后庙17A可知红香炉天后庙肯定在殖民地时代之前已存在。
红香炉天后庙
红香炉天后庙创庙于何时,今不可考,但按庙宇一般发展规律,多从简陋的神龛开始,善信渐多,香火渐盛,便由善信集资兴建一所庙宇,供奉神只,香客日众,庙宇变得狭窄,不敷应用,再由善信挥金扩建,红香炉天后庙,正经历了这条发展轨迹。
要追溯红香炉天后庙创庙年代,发展过程,须从庙内文物-特别是碑记入手18,现存庙中年代最早文物是乾隆十二年岁次丁卯(1747)的钟,是由船夫所捐赠,但钟上并无注明是否为此庙铸造,故此它是否红香炉天后庙之原物无从稽考,但按庙内现存最重要的文物及资料来源:同治戊辰(1868)的碑记所记述,该庙在道光甲辰(1844)曾重修,重修后的庙宇,仍属"狭隘之形",则可推知未重修前,即1844年以前的规模是较小的。庙前的石狮,刻有"兴邑刁爵"字样,是道光廿五年(1845),即第一次重修后翌年奉赠的。同治七年(1868),即距第一次重修24年后,红香炉天后庙进行了第二次的重修,这一次重修,"蒙阖港水陆商民人等,挥金相助",规模宏大,奠下了目前所见的规模。同治戊辰的重修碑记,不单记述了该庙重修之原委,还附有详尽的捐者芳名,不单是研究该庙历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,它对于探讨19世纪中叶香港华人社会也甚具参考价值。
从碑记所录的捐者芳名,我们可以知悉红香炉天后庙是19世纪中叶港岛上最重要的庙宇之一,具体分析如下:
碑记上说该庙重修,"叨蒙阖港水陆商民人等,挥金相助",而从碑记中的善信芳名观之绝非夸大。碑文所录捐钱资助红香炉天后庙进行重修的善信连公司共1,418名/间、筹得善款共4,483.5圆,无论从善信数目,以至所筹金额来说,均为当时全港庙宇之冠。
阖港水陆商民人集资重修红香炉天后庙
细读碑文中所列商号芳名,如恒丰行、合兴行、永祥顺、元发行、得美行、广福利、泰丰顺、建南号等,均为当年香港最具规模的南北行庄。其中除建南号(为严道南所有,严氏在东华医院落成典礼上宣读祷文,是华人领袖之一)外19,余均为潮籍商人,曾资助兴建广州潮州八邑会馆20。至于其他商号,仍有不少属于潮籍。虽然此碑所列商号人名众多,除潮州商号较易识别外,其他的无从推断其乡属,故不能断言天后庙的捐助人中以潮州人为最多,但捐钱60圆的7间商号里,已知有5间肯定是潮州人开设的行庄,比例极高,福茂隆捐70圆,为捐款者之冠,推断可能也是潮福人士所开办。这反映了潮商的富有及南北行庄在1860年代晚期渐趋蓬勃。查南北行是在1850年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,在1860年代成为香港华人商业经济中一股强大的力量21,必须指出:南北行商人组成的南北行公所,正是高满华、招雨田、陈焕荣、陈春泉等殷商在1868年成立的22,与红香炉天后庙重修适同一年,遍查港岛其他庙宇碑记,包括文武庙在内,都找不到如此众多南北行商人集资修缮庙宇的例子,这是可堪玩味的。
红香炉天后庙的资助重修善信中,包括两间业缘组织,即番衣行联聚堂和石行联盛堂(他们还捐赠了对联及石台),这是香港开埠以后最早成立的行会,惜其名称只保留在庙宇碑文中,其具体组织性质如何,已不可考。但打石是开埠初期最蓬勃的行业23,其最早成立业缘组织,理所当然。
捐款善信,包括了本地的商号、坊众(黄泥涌村众)、机构(乐善堂)、货船(金和丰、金利丰船等)、栏栈(兴隆栏、仁安栈等),林林种种,既反映了香港商号日益增多,经济日趋发达,也印证了重修红香炉天后庙的确是阖港水陆商民人等集资玉成的。
细观捐款名单,其中还包括了台湾、潮州、澄海、省城、留隍、金山等地的商号和善信,而且为数不少,已超越了本港范围,此庙宇远近驰名,可以想见。这也是当时其他庙宇不可企及的。
同治戊辰年的红香炉天后庙的总理和值事,名单中包括了上面提及过的恒丰行、合兴行、元发行等首屈一指的潮籍南北商号24,其余商号及人士中,有四名是姓戴的,这反映了该庙庙祝所指称该庙为戴姓族人所创建,似不无道理。查该天后庙的业权至今仍为戴姓族人所拥有,1928年通过的华人庙宇条例,规定全港庙宇应由华人庙宇委员会管理,但红香炉天后庙获豁免,仍由戴氏族人自行管理,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。25
红香炉天后庙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
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,城镇有社学及学宫可供地方缙绅集会;在乡村,同姓乡绅可在宗祠内集议乡中事务,然而不同姓的乡村父老,多假土地庙或文武庙集会,庙宇还成为赈米、施药、敬老、恤孤等福利事业的发起机构;且乡中诉讼纷争,都由父老在庙内排难解纷,主持公道。26香港开埠之初,香港政府对华人不干涉政策,华人往往自行处理自己事务27,其中最普遍的一种组织,便是庙宇委员会。1847年兴建的文武庙,原是太平山地区华人集资兴建的庙宇,1851年扩建后,逐渐发展为上、中、下、西四环坊众拥有的"阖港文武庙",庙旁的公所,便是坊众聚会商议地区事务的中心。28在19世纪中叶,香港仔的天后庙、鸭脷洲的洪圣庙、赤柱的天后宫、湾仔的玉虚宫、洪圣庙、筲箕湾的天后宫都是地区坊众集会的中心29,庙旁设有公所,便是坊众议事之地。这些庙宇捐款的善信,多是街坊或渔民,修建庙宇的款项,都是集腋成裘,募捐得来的,筲箕湾天后宫光绪二年(1876)重修碑记上所谓"独念我湾地介一隅,家非万户,连年告助,巨款难筹,抑知各共一心,蚨钱难掷"30正是忠实写照。这些庙宇,带有浓厚的地区色彩。但反观红香炉天后庙,其所在地区,人口不多,在19世纪中晚期,天后庙所在地区,已在维多利亚城范围以外,相当偏僻,但捐钱重修的善信,既不局限于本区居民,甚至包括香港以外的人,捐款来自各式各样的行业、商号、机构、行会,而庙宇旁边没有公所之设,可知它不属于街坊的庙宇,其地位在19世纪中晚期的香港,只有文武庙可以比拟。所谓"蒙阖港水陆商民人等挥金相助",没有半点夸张。从红香炉天后庙的例子,可见在19世纪的香港,庙宇通过宗教活动是华人社会里唯一能打破血缘、业缘和地缘藩篱的组织,难怪能长期在香港华人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注释
| (1) | 参见拙文:(鸦片战争时期琦善和义律有关"香港"定义的争论),发表于"香港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",1997年12月,未刊稿。 |
| (2) | 参考饶宗颐:(港九前代考古杂录)见《岭南文史》,1985年2期(1985年12月),页46、50。 |
| (3) | 引自阮元:《广东通志》卷175(经政略)18,(兵制)3,大鹏营及水师提标左营条。 |
| (4) | 关于陈伦炯的《海国闻见录》的海图,详见哈尔.恩普森着:《香港地图绘制史》(香港:香港政府印务局,1992年)。 |
| (5) | 见王崇熙等编:《新安县志》(嘉庆廿四年〔1819〕刊本精钞),附图。 |
| (6) | 此图标出了许多军事建置的所在,凡炮台或汛站,多标上营汛旗杆标志以作识认。 |
| (7) | 有关此等现存海外的海图资料,详见李孝聪着:《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 |
| (8) | 见《香港地图绘制史》,页30。 |
| (9) | 同注(5),卷2 (舆地略),(都里条)。 |
| (10) | 引自文庆等(编):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》(北京:故宫影印本,1930年)卷30,页17。 |
| (11) | 见佐佐木正哉(编):《鸦片战争之研究(资料篇)》(东京:近代中国研究社,1964年)页75。 |
| (12) | Chinese Repository, May 1841,pp. 287 - 289,有关香港开埠前后岛上各区之状况,可参考James Hayes, "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",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.24, (1984), pp.105-140. (Hereafter as JHKBRAS)及A.R.Johnston, "A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", Hong Kong Almanac and Directory for 1846 (Hong Kong: The China Mail, 1846). (Hereafter as "NIHK") |
| (13) | 见丁新豹(编):《河岳藏珍:中国古地图展》(香港:香港博物馆,1997年)页86、87、92。 |
| (14) | James Hayes, "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, Tam Kung Temple, Happy Valley, and Tin Hau Temple, Causeway Bay, Saturday, 7th November, 1970", JHKBRAS Vol.11(1971), pp.195-197。 |
| (15) | 引自夏历(梁涛)着:《香港东区街道故事》(香港:三联书店,1995年)页185。此书对于红香炉汛与红香炉天后庙之关系有详尽记述,但指称红香炉天后庙原为汛房,则似缺乏证据,流于臆测。 |
| (16) | 同注(14) |
| (17) | "NIHK";E.J. Eitel, Europe in China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3) (1st published, 1895), p.190. |
| (18) | 有关红香炉天后庙之文物,包括同治戊辰碑记,详见科大卫、陆鸿基、吴伦霓霞合编:《香港碑铭汇编》(香港:香港博物馆,1986年)册1,页129;册3,页666,859,860。 |
| (19) | 见《东华三院百年史略》,上册,页91。 |
| (20) | 此等商号,除建南号外,均见于潮州八邑会馆之碑记,见(香港潮人商业调查概况),载《旅港潮州商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》,(香港:旅港潮州商会,1951年)页1-20。 |
| (21) | 关于1850年代以后南北行之兴起,可参考拙着:《香港早期之华人社会1841-1870》(博士论文,未刊稿)第三章,页336-344;第四章,页454-468。 |
| (22) | 香港南北行公所(编):《南北行公所新厦落成暨成立86周年纪念特刊》(香港:南北行公所,1954年)页23。 |
| (23) | 有关香港早期之打石行业,详见罗香林:(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迹及其与香港建设之关系),《食货月刊》1:9(1971年12月)页459-463。 |
| (24) | 其中高满华的元发行是南北行的滥觞,详见高贞白:(从香港的元发行说起),《大成》117期(1983年8月)页47-52;118期(1983年9月)页45-51;119期(1983年10月)页34-39;120期(1983年11月)页46-54。(高资政公阡表与高楚香公家传),《大成》121期(1983年12月)页50-59。 |
| (25) | James Hayes, "Visit to the Tung Lin Kok Yuen, Tam Kung Temple, Happy Valley, and Tin Hau Temple, Causeway Bay, Saturday, 7th November, 1970", JHKBRAS Vol.11 (1971), pp.195-197. |
| (26) | 夏历(梁涛):(文武庙与香港教育)(香港街坊志)(文汇报)1982年6月18日-7月22日。 |
| (27) | 有关港英政府早年统治华人的政策方针,详见注(4)拙论文。 |
| (28) | 有关文武庙的起源及在十九世纪香港所发挥作用详见上注。页181-186;360-363。 |
| (29) | 有关资料可参考Carl T. Smith, "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", JHKBRAS Vol. 13 (1973), pp.133-139,其中湾仔洪圣庙见同作者的"Wanchai -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"in Elizabeth Sinn (ed.) Between East and West: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(Hong Kong: Centre of Asian Studies, Hong Kong University, 1990), pp.47-93. |
| (30) | 光绪二年(1876)的(天后古庙重修碑记)同注(1),册1,页167。 |